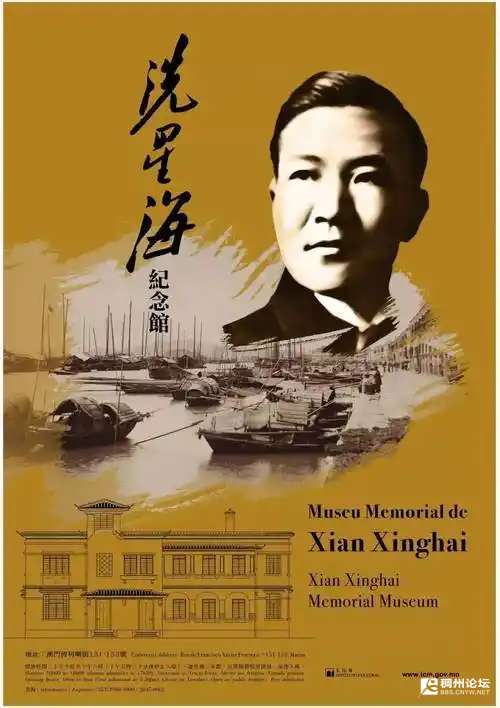1939年的延安,窑洞外的黄土被秋风卷成细沙,打在窗纸上沙沙作响。冼星海攥着那几张写满歌词的稿纸,指腹磨过"风在吼,马在叫"的字样,指尖的冻疮裂开细小的口子,渗出血珠也浑然不觉。
几个月前他从巴黎辗转回到祖国,轮船刚抵香港,就听见码头工人哼着不成调的救亡曲。那些粗糙的旋律里裹着炮火的焦糊味,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。他扔掉了准备好的西洋乐总谱,带着一把旧小提琴钻进了北上的卡车,车辙在尘土里画出的曲线,像极了他跳动的脉搏。
延安的冬夜来得早,他住的窑洞四处漏风,钢笔水常常冻成冰碴。光未然把《黄河吟》的诗稿送来那天,正赶上他发疟疾,裹着三层棉被还在发抖。可当"黄河之水天上来"的句子撞进耳朵,他忽然掀开被子坐起来,赤脚踩在冻土上,在墙上比划着旋律的起伏。油灯的火苗被他呼出的热气吹得摇晃,把影子投在土墙上,像一群挣扎着向前的人。
没有钢琴,他就趴在炕桌上写谱,用吃饭的搪瓷碗敲打出节奏;没有乐队,他就拉着警卫员、学生、炊事员一起哼唱。有次排练到深夜,伙房的老张端来一锅洋芋,蒸汽里混着他沙哑的嗓音:"要的就是这种劲儿!像黄河的石头,砸在地上能冒火星子!"
那年春节,中央大礼堂的土台子上挤满了人。当第一声小号划破夜空,台下忽然安静下来。冼星海站在台侧,看着乐队里那些拿惯了锄头和步枪的手,此刻正握着乐器。当"保卫黄河"的合唱声浪翻涌起来,他看见前排的老战士悄悄抹了把脸,浑浊的眼睛里映着台上的灯火,像两簇重新燃起的火苗。
有个十五岁的小通讯员,总躲在排练室外听。有天冼星海叫住他,发现少年冻裂的手里攥着根树枝,在地上画着五线谱的模样。"想学?"他笑着把自己的旧毛衣披在少年肩上,"等打跑了鬼子,我教你拉小提琴。"少年红着脸点头,转身时衣角扫过地上的树枝,在黄土上划出一道昂扬的弧线。
后来这曲子传到了前线,有战士在冲锋号响时,会跟着喊出"风在吼"的调子;有伤员躺在担架上,用微弱的声音哼着"我们是黄河的儿女"。冼星海收到过一封从前线寄来的信,信纸被血渍晕染了大半,字迹却依旧有力:"听着您的歌,我们觉得黄河就在身边,浑身都是劲。"
1945年的春天,冼星海躺在莫斯科的病床上,窗外的积雪正在融化。他已经很虚弱了,却总让妻子把收音机放在枕边。当电波里传来隐约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时,他枯瘦的手指在被单上轻轻打着节拍,像在抚摸祖国的土地。弥留之际,他喃喃着"黄河...还在流",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,却重得能掀动万里波涛。
如今延安的窑洞早已换了新颜,但每当风吹过黄土高坡,仿佛仍能听见七十多年前的旋律。那些从窑洞里飞出的音符,早已汇入真正的黄河,随着奔涌的浪涛,永远激荡在民族的血脉里。